推薦
作者:阿莫
來源:界麵文化
(ID:BooksAndFun)
編輯:
阿九
既然人類本性中血腥殘暴的部分從未消失,
那就在遊戲中去釋放吧。
● ● ●
“大吉大利,今晚吃雞”:
廝殺毀滅同類的遊戲為什麽會流行?
在網絡上,“吃雞”這個乍一聽莫名其妙的詞已經紅遍半邊天。該說法來自於一款名叫《絕地求生》的遊戲。這是一款玩法直白簡潔的“大逃殺”類遊戲,每局遊戲100名玩家參與。玩家被飛機投放到孤島上進行對抗,所有裝備隻能通過搜刮地圖和劫殺其他玩家獲得。
玩家不分陣營地相互殘殺至隻剩一人存活為止,最後幸存者屏幕上會出現:“Winner Winner,Chicken Dinner”的勝利標語,翻譯成中文就是“大吉大利,晚上吃雞”,因此也被稱作“吃雞”遊戲。
“吃雞”的熱潮迅速蔓延,不少遊戲主播早已投入到的戰鬥中。除此之外不少名人,例如林更新、陳赫、王思聰等也經常組隊玩《絕地求生》。各大網吧裏,“吃雞”成了最受歡迎的選擇。截至10月17日,《絕地求生》總玩家人數達到1645萬人,購買賬戶人數達到1656萬人。其中中國玩家占了近乎“半壁江山”,占總數的41.62%。
據估算,中國用戶僅購買遊戲便花費近6.7億元人民幣。毫無疑問,《絕地求生》已經成為了繼《王者榮耀》之後的又一大現象級的遊戲,到底這款射擊遊戲是為何能夠風靡全球,讓人們如此著迷?
全民吃雞時代:
“大逃殺”如何在遊戲界崛起
“吃雞”遊戲的狂潮令玩家如癡如醉。在沒有國服版本的情況下,大部分中國玩家就算花高價且隻能依靠不穩定的加速器,也要玩上一局。麵對超強的吸金能力和國內市場的空白,嗅覺敏銳的國產遊戲廠商紛紛入局,推出了類似的遊戲產品。國內大逃殺遊戲的大網已經鋪開,並且即將迎來新一輪高潮。
今年10月18日,《小米槍戰》開始安卓端單排內測,內測中單日最高活躍用戶就達到了100萬。緊接著,網易出品的《荒野行動》安卓版開測。網易的另一部類似作品《終結者2:審判日》11月4日登陸全平台,預約人數超300萬。不遑多讓,騰訊也相繼開放《光榮使命》和《CF荒島特訓》兩款“吃雞”手遊,《光榮使命》預約人數超過400萬,《CF荒島特訓》預約人數則超過了1000萬。
國內的瘋狂現象並不是例外,其實早在此前,大逃殺類遊戲就已經在國外爆紅,引起關注。最早的起源可追溯到2013年,遊戲平台steam上的設計師Brendan Greene在知名步行模擬遊戲《arma2》中上傳了一款與2000年的日本電影《大逃殺》同名的自製遊戲模型——Battle Royale模組。
由此,大逃殺遊戲初現雛形。接著,2015年,遊戲製作商SOE推出《H1Z1:殺戮之王》,充分發展了末世環境下人類互相殘殺的模式。極端的遊戲形式配合直播行業的發展,一時間人氣斐然。在此之前,射擊遊戲已經多年沒有改進,正陷入雷同的低潮,而這種讓玩家沒有組隊意識的新設定,恰好帶來了一場翻天覆地的進化。
傳統的FPS遊戲(First-person shooting game,第一人稱射擊遊戲)中,規則設定多為執行任務、殺怪物等,往往需要團隊合作共同取得勝利。隻要隊伍中有一個隊員最終戰勝了對方,就算作整個隊伍勝利。而大逃殺遊戲設定是純粹的暴力和殺戮,不存在配合與犧牲。
赤裸的強弱法則和直接、自由的遊戲體驗給予玩家更直觀的刺激。同時,大逃殺類遊戲的地圖非常廣袤,玩家人數遠多於其他類型遊戲,戰鬥強度大。安全區、轟炸區、空降補給和物資的不規律分布等不確定因素也讓其兼具了極強的娛樂性。
《絕地求生》遊戲截圖
一年後,Brendan Greene和藍洞公司合作發布了更加完善的《絕地求生》,精簡了《H1Z1:殺戮之王》中的任務要素,更進一步強調戰鬥性,終於引爆大逃殺遊戲的狂潮。《絕地求生》發售後連續十五周登頂steam銷售榜第一。2017年9月中旬,其同時在線人數超過130萬,刷新了Steam平台曆史上在線人數的紀錄。
之後,大逃殺類遊戲幾乎逢出必火。就連碌碌無名的小廠商 Xaviant 開發的大逃殺類遊戲 《淘汰》上線1個月也收獲了57萬玩家,銷售額超過1400萬美元。、隻要這種類型繼續火熱下去,未來還會有更多的同類型遊戲陸續推出。
不難注意到,大逃殺遊戲在傳統遊戲上做了“減法”後,才從眾多的 PVP(player versus player,意為玩家互相對抗)型網遊中異軍突起,獲得勝利。布局謀劃、合作協力、聯合戰術等等以往常見的規則都被去除,剩下的隻有PVP遊戲最核心的要素——對抗和獲勝。在大逃殺遊戲的“進化過程”中,這個核心要素更是愈發突出。
《絕地求生》去掉了《H1Z1:殺戮之王》中采集、合成、獲取水分和飽食等等任務,消滅了一切“無衝突性生存”的可能性:要生存就要殺戮和搶奪,要存活就要擊殺、躲過敵人,同時戰勝毒氣和陷阱。沒有任何人值得信賴,沒有任何方式可以和平共處。

正是這種純粹的對立感和獵殺感在吸引廣大受眾——高強度和快節奏對抗中,大部分玩家甚至不能撐過開場的五分鍾,極大加強了幸存者的成就感。每一個玩家都渴望打敗其他99人,成為唯一還能站立吃雞的勝者。
大逃殺概念的產生與發展
獨自為戰,戰勝同類的對抗性可以說是“大逃殺”這一概念的本質。“大逃殺”(Battle Royale)概念最早來自日本作家高見廣春的暢銷小說,描述了一群中學生被獨裁政府強迫投入一場淘汰賽自相殘殺,直至隻剩1人存活。後來這部作品被改編成電影,其充滿“暴力美學”的鏡頭和極致的情節大為出名。此後,這種互相砍殺,戰至最後一人的模式就被稱為“大逃殺”。
大逃殺起源的小說背景原本和日本沒有關係,但是其反映的不少現象確實體現了社會問題,例如當代社會的壓力以及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間的矛盾。在電影中,孩子們被迫參與大逃殺的緣起是日本經濟崩潰,少年犯罪率上升,成年人用大逃殺來教育孩子們——大逃殺是一次淘汰賽,是逼迫年輕人成長的機會也是為社會做刪選的基本考試,將不適應生活的弱者淘汰掉,留下真正有用的人。
在日本,整個社會的壓力非常大,但幾乎沒有針對老年人與小孩的。可以說,日本的社會壓力基本呈現“n字”形——少年和老年時壓力小,中年時壓力和管束最大,無論是法律還是輿論對青少年都很寬容。也許正因如此,日本有很多校園暴力、青少年犯罪、街頭小混混、少女援交等未成年人問題。這些張狂又不用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的未成年人很容易引起成人的不滿和恨鐵不成鋼的情緒,希望能夠有一種方式快速有效地“教訓”一番。
於是,影片預設了一種極端的情況,就是把不知世事的孩子們投入殘酷的社會規則中,使用極致的暴力,以一種誇張的形態模擬了成人世界的廝殺,例如有限又隨機的資源、友情和利益的抉擇、信任與反目……隻有斬除天真,獲得勝利的人才有成為“社會人”的資格,《大逃殺》看似荒誕離奇的血腥內容,實則是對現實社會的隱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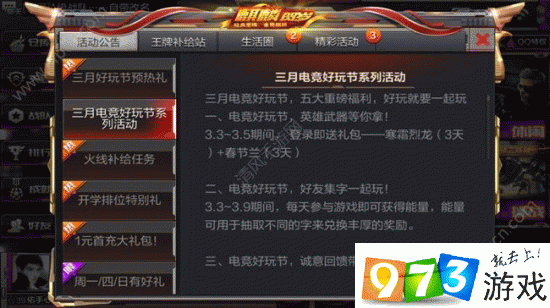
《饑餓遊戲》劇照
另一部經常被拿來放在一起討論的電影,是2012年好萊塢的《饑餓遊戲》,講述了一群年輕人被強製在直播下戰鬥殺死對方的故事。兩者題材內容看上去非常相似,但是其實核心思想並不相同。如果說《大逃殺》是用扭曲的比賽展現當代社會的殘酷,《饑餓遊戲》則接近於對未來反烏托邦的想象,其主要思想是對獨裁政府和階級壓迫的焦慮。
貧民血淋淋的互相廝殺隻為了娛樂上等人的生活——影片用這種誇張的方式展現出對社會的擔憂,追問文明和科技高度發展之後,世界會不會反而進入一個貧富差距過大、階級壓迫與階級鬥爭更明顯、弱肉強食更直接和殘忍的叢林式社會?當然,劇情中還要加上一些親情、愛情、個人英雄主義等等好萊塢電影屢試不爽的雞湯主題。在這裏,主人公的青少年設定並不是為了將成人與未成年人劃分開來,似乎更多是呈現年輕俊男靚女的借口。
雖然《大逃殺》與《饑餓遊戲》有著諸多不同,但它們確實都體現了“封閉環境內殺戮直隻剩一人”為主要邏輯的模式以及其獨特的魅力,即在作品中展現了一種人為創造的原始叢林。通過設定這樣一個有著殘酷規則的叢林,極度誇張的戲劇性發展,道德感的衝突和感官上的刺激性都可以逐漸迸發,實在是吸引觀眾的大好題材。
因此在不少電影作品中都出現過:2007年的《死刑犯》講述了一群死囚犯被賣給節目組,節目組通過直播他們在孤島上的廝殺來賺錢的故事;2008年的《死亡飛車》中,罪犯被迫參與一場極為暴力的賽車比賽;2016年,《貝爾科實驗》裏,一個公司的白領們被要求在辦公樓裏和同事互相戰鬥……
黑暗叢林為何如此迷人?
事實上,人類觀看同類戰鬥至死的曆史極為悠長。古代羅馬為紀念勝利驅使8萬猶太俘虜修建大鬥獸場。成百上千的奴隸和野獸投入其中互相廝殺, “歡慶”帝國的勝利。這樣的廝殺持續了數百年。一旦進入鬥獸場,奴隸們的人生意義就是不斷廝殺,讓圍觀的貧民和貴族取樂。
而觀看搏鬥的人內心可以充滿種種複雜的情緒:血腥場麵帶來的感官刺激、不確定結果的猜測和緊張、看到激烈拚鬥的激動、對同類殘殺的恐懼、因受害者不是自己而感到慶幸……可謂是非常特別的體驗。也許這就是觀看大逃殺模式的迷人魅力。
現如今,時代改變了,人性卻依舊如昨——人們還是喜歡看極致的慘劇,隻要主角不是自己。在影視和遊戲的幫助下,身處文明社會的我們已經能夠在不真正傷害他人的情況下,“充滿人道主義地”觀看同類互相殘殺。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大逃殺模式中的黑暗森林的流行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困惑與迷惘:已經逐步建立了現代文明社會的人們,為什麽還會對原始叢林式的殘酷狩獵、互相廝殺充滿深情地一再回望?
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提出“自然狀態”理論,他認為,在人類沒有國家強製力的束縛的自然狀態下,每個人有著自由、平等的權力。但同時,每個人都隻有對立而沒有合作,很容易“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霍布斯還在其著作《利維坦》中指出:“人人相互為戰的這種戰爭狀態,還可能產生一種結果,那就是沒有任何事情是不公道的。在這兒不會存在是和非以及公正與不公正的觀念。缺乏共同權力的地方也就沒有法律,沒有法律的地方也就無所謂公不公正。” 也就是說,整個社會所呈現的支離破碎的體係和絕對的混亂。
霍布斯設想的自然狀態是否在人類曆史上存在過,其實有待商榷。但看上去雜亂無章,對身處其中的人們沒有絲毫保障的恐懼,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又顯得相當迷人。
20世紀中葉,英國作家威廉·戈爾丁寫下著名小說《蠅王》: 世界大戰爆發,政府將兒童疏散到邊遠地區。一架運輸機墜毀在一個荒島上,大人都死了,隻剩下一群小孩。荒島上有充足的水和食物,形成一個遠離現代文明的“孩子王國”。孩子們分成兩派,守序派要求大家像在文明社會裏一樣生活,例如飯前洗手、在固定地點如廁、遇大事開會討論等;混亂派則希望隨心所欲。兩派為了爭奪主導權發生了衝突。很快,人多勢眾的混亂派占了上風,依靠自己的暴力推翻了守序派,並且在追捕對手的過程中燒毀小島,隻留下一片荒涼。
不過,二十世紀以來,大規模對人類生命的安全常常不是混亂狀態帶來的。大屠殺、集中營、戰爭和暴力,往往都以社會組織的形式存在。這難怪人人持槍的社會會被某些人奉為保持和平的典範——人人都具備摧毀對方的能力,因而也就能相安無事。而在這個圖景另一邊,則是控製個人暴力的理想——用政府和社會機構上繳個人自衛權,形成社會的公序良俗。
但正如大逃殺文化在日本所展現的那樣:如今社會的弱肉強食,遠遠不再是黑暗叢林的形式,也不再是“多數人的暴政”,它是成年人的生存法則,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廝殺。
而在遊戲中,人們以最激烈的符號表達和最不涉及現實的休閑方式,一次又一次地經曆“殘酷”。
● ●●
1
你可能會喜歡:
社會學了沒



